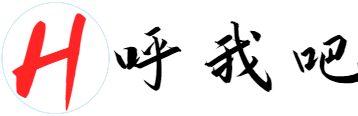假设我是一只鸟,我应该用沙哑的喉咙歌唱。
妈妈是护理,我也常到医院散步。充溢生命气味的走廊,显得静谧和繁忙,科室里的呼应器像是调好的隔几会儿响一下,没几分钟,护理都仅仅奔忙在这无尽头的长廊上。我开端在走廊上逛荡,每走过一个病房,总觉得自己的身上聚集了一种特殊的目光——我的神态格外地自如。
“护理!护理!快点快点!”一个中年女子在病房里大叫,呼应器不停地响。
护理和医师像一股激流都朝那个方向奔了曩昔,走廊上除了医务人员也就别无别人,这好像已是常事。
走廊外的雨开端下了,鸟被迫地离开了自己的巢。
这被暴风雨所冲击的土地,这永久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拂晓。
只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躺在病床上给推了出来,药水瓶滴答地滴着药水。地板好像轻轻地震动了,他们走地很重,病床旁的几个中年女子跟着病床跑,她们的眼泪将雪白的被子模模糊糊地感染上了灰色。有一个在抽泣,她一向握着老人的手,她用袖子拂去脸上的泪水,可泪水又不住地涌了出来,她干脆就把手放在了腮旁边。还有几个,眼泪带起了嗓门的大开,伏在病床旁边,用方言喊着。那声响在长廊上格外地响,更是传来一阵阵回声。
她们坐在急诊室门口的,也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迷茫地坐在凳子上,她们抱着孩子就像抱着期望相同。
雨逐步大了起来,人们开端四处窜逃,鸟消失地无影无踪。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里面。
好长时间往后,急诊室的灯总算灭了。医师一出来,人都围了上去,小孩原本还想坐在凳子上,却被大人给拉到了医师面前。声响先是从前面传来,再是后边,医师对家族说了几句,又从这些人中间挤出一条缝,深陷于这个当地。他们登时变成了雕塑,更有几个靠在了墙上。眼泪就在那时停止了,搭在小孩肩上的手也落了下来。什么都静了。
病床推了出来。那些人无力地抱着床上的人,已经摊在了地上。
雨停了,只不过乌云还在,鸟还没回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由于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一个人死了,具有了如此多的泪水算是值得了。
又过了好久,我趴在露天走廊上的沿上。树叶都零零落落地散在地上,可贵看见几朵花依靠在大树根旁——土地是最柔软的。从未这么深深地感触过生命如此珍贵,曾经仅仅把它作为语文书里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死了今后,要回到土地,回到我最初日子的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