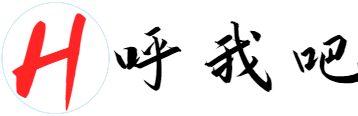那一片绿,一件青布褂啊,如一首老歌留在回忆深处。风日清和,天高云淡。
以后的每一天,“那件青布褂”总会出现在相同的当地,见咱们走来总是停下手中的活儿,友爱地笑笑,示意咱们先走。咱们便低着头闪开,再不多逗留。
那日,我在校内乱走,连日来的各种不顺让我备受煎熬,真想蛰居蛰伏。忽然一阵嘹亮的歌声传来,像是一首叫《小白杨》的老歌,虽不似流行音乐带着温情和悠远的空灵,却嘹亮明快纯洁有力,那种质朴与高兴,让我暂时忘了自己的烦恼。寻声找去,眼前竟是那个“青布褂”的背影,他正蹲在一个平房后的旮旯,伺弄着用抛弃的塑料盆栽种的植物,那件长褂几占据了他整个人,更显消瘦。他正被满眼的绿包裹着,有绿萝的盛开的新绿,有吊兰肆意上扬的翠绿,有常春藤愤怒的发芽拔叶毫无忌惮爬满半面墙的墨绿,深探浅浅的绿色汁液在流淌,春在这个旮旯生机盎然。
从那以后,我总要去看看那片绿,就像那件“青布褂”,卑微低下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地生长。那歌声,那片绿,那件青布褂由此住进了我心里,特别在困顿时我总能想起他。
那一片绿,映衬着那件“青布褂”,在我心中早已幻化成一首歌,知足高兴便是庆生最好的情调啊!
那天,当我第一次站在这所百年老校里,也第一次见到了那件格格不入的“青布褂”我置疑他是否归于这个时代,一个身着那样一件老旧青布褂工衣,露出半条广大的黑布裤和一双再简略不过的老布鞋的男人。他五十多岁的样子,两只手正用力握着他样干燥的大扫把。我猜测他应该是校园的勤杂工。
愁云惨淡,繁华殆尽。
“你怎样在这儿?”他总算发现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植物长得真好。”我没接他的话茬兀自说道。“是啊,当初种它们便是觉得好养,插一株就能长成一片。”他朝我笑笑,“还能跟我做个伴儿,每天看它们就像看着儿孙一天天长大。”“他们没跟你住一起?”我与他扳话起来。“他们在外地,我还不老,还能养活自己,且要好好儿活着呢!”他他动身的那一刻,我呆住了,这么久从未留心过他的右腿竟是残疾。“您?”他看出我的惊异,“还好,习惯了。不管怎样咱都要有盼头地活着,不是吗?”他像孩子般笑了,唱着那首老歌一瘸一拐地挪开了,我不敢相信这份养花的闲情,高兴的歌声竟出自于这样一个勤杂工残疾人,他竟能如此淡定平静地倾诉自己的故事。跟他比,自己的那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烦恼消散了。
暖阳拂身,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