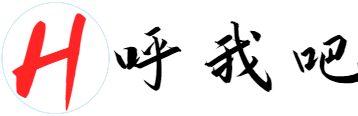在《幼年趣事》那篇文章中,我提到过我的家境。那时分,我享受着爸爸妈妈和大爹大妈的两层宠爱,什么事情都由着我,即使做错了什么,也至少有一方“罩”着我,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不要说挨揍,就连一句重话气话,好像也没有受过。
咱们那儿是一个四合大院,聚居着同族的好几户人家。跟一般的四合院不同的是,咱们的宅院处于一个乱石窖的中间,远离地步,四周绿树环合,显得格外清幽僻静。加上斜度比较陡,宅院又比较大,所以,正房一面就比其他三面要高出一米多。造屋的长辈们就地取材,在正房前面修砌了六步与院坝等长的石梯;对面是吊脚“虚楼”,中间是宽大的“曹门”,与正房中间的“堂屋”相对;“曹门”外是十一级“排码梯”;宅院中间是宽大的“地坝”,“地坝”和阶沿全都铺着光洁的大石板;宅院外还铺了好几条出入的石板路。由于咱们宅院大,人又多,路也好走,所以,每逢农闲的时分,生产队其他宅院的人,都喜欢到咱们宅院来玩。
那时分不兴什么计划生育,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孩子。那时分也底子没什么幼儿园,所以,上小学一年级前的那几年,全都是咱们小孩子的自在六合。我是咱们宅院里最大的孩子,成天领着一大帮弟弟妹妹们在院坝里和院外的树林草丛和乱石窖中疯玩。无形之中,我成了他们中的“孩子王”,什么主意都由我定,什么事情他们都百分之百地遵从于我。
大约是六、七岁的时分,好像是一个夏天,离咱们最近的一个宅院里回来了一位叫陈先华的复员军人。由于同姓,辈份又比咱们高,大人们让咱们喊他“公公”。他虽然是个长辈,又是个大人,但毕竟年纪不是很大(大约不满20),就像一个大小孩相同,所以,一来二往,咱们就很熟了。
一天晚上,天上挂着圆圆的月亮,咱们一大帮孩子在宅院里干净的石地坝上,围着先华公公要他给咱们讲故事,然后又一同玩游戏,最终,干脆打起“仗”来了。咱们五、六个大一点的孩子一伙,攻击先华公公那个“光杆司令”。咱们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不过,他也许是心存顾忌,不敢对咱们下重手,而咱们呢,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使出了浑身解数,奋不顾身地朝他身上乱扑、乱打,所以,他也占不了多少上风。
那晚上的详细细节,我早已模糊不清了,只记住咱们玩得很晚,很疯狂。后来,他要回家了,可咱们还意犹未尽,缠着他不放。他又跟咱们玩了一瞬间,趁咱们不注意,忽然挣脱开来,一会儿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这可把咱们给气惨了,拼命去追他,但哪儿跑得过训练有素的军人呢?没办法,咱们只要使出咱们的“杀手锏”了,那速度,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长跑冠军能比得上——声响,他跑得过声响么?所以,在我的带领下,参战的,观战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一同大声叫骂,喊着他的姓名乱骂一通,直到他的消失在对面山头之后,咱们还骂个不断,大有非把他给骂回来不行的气势。那时分,谩骂在农村是很平常的事,并且,骂的花样繁多,骂的力度也是不行低估的。那一晚,咱们几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真是把平日里从大人那里学来的谩骂“绝活”全都给用上了,骂的那些话,真是连“牛都踩不烂”的。
但是,就在咱们为自己的“精神胜利”而自鸣满意,还没来得及鸣锣收兵时,十来个大人忽然出现在咱们的面前。他们将咱们一个个不由分说地拖回了家,紧接着,就从各家各户里传来了大人厉声的喝斥和小孩挨揍哭泣的声响。
我被父亲拽回家里,摁在火坑石上跪着,打完屁股打手板。我声泪俱下,呼爹唤娘,一双眼睛在四下里寻求保护。但是,就连一贯疼我爱我的大爹大妈,此刻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点点没有为我护我的意思。后来,父亲打我的速度和力度渐渐地慢了下来和轻了下来,边打边给我讲道理,一旁的大人们也帮着父亲经验我。我也渐哭渐止,渐渐理解了自己的过错地点。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谩骂了。起初是不敢骂,怕挨揍,不过,在背地里曾鼓动过弟妹骂他人;再后来,是不愿骂,由于自己懂事了,真心实意地想做一个文明人。
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终一次挨揍的难忘经历。